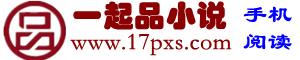第710章 火种,西行
作品:《大清要完》 最新网址:www.xs.fo</p>长安城外。
春日的关中平原本该是麦苗返青、生机勃勃的时节,可此刻的长安城外,却是一片灰蒙蒙的尘土飞扬。数十万人、数万辆车马,如一条蜿蜒的巨龙,缓缓向西蠕动。
士绅们骑着瘦马,穿着孔子服,腰悬宝剑,头顶发髻,身后跟着坐着双轮小马车,里头都坐着抱着金银细软家眷,还有一些个衣衫褴褛的奴仆,推着满载书籍、祖宗牌位和口粮的独轮车。他们往往以乡为单位编成队伍,逶迤西行,三步一回头。
孔繁灏带领的山东孔家圣裔队伍无疑是西行的名教大队中最为显眼的,数百辆马车在官道上排出一长列队伍,前后还有腰带上插着转轮枪的孔府骑士护卫——这些个转轮枪都是照着上海江南制造局出品的天历四年造转轮枪手搓的,虽然有点糙,零部件也很难呼唤,根本算不得工业化产品,但是拿来在中亚“护道保教”应该是够了。
不过这些从山东一路跟着跑到陕西,现在又踏上漫漫西行路的孔氏族人们,一个个脸上都写满了惶恐不安,不时回头,望着阳光底下雄壮巍峨的周都长安。
孔繁灏乘坐着一辆比寻常两轮马车大了不止一号的大车,车辕上挂着“衍圣公府”的匾额,车帘紧闭,里头的衍圣公仿佛不愿多看这乱世一眼。
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李鸿章从碎叶带来的“洋枪骑士”——他们穿着半旧的棉甲,背着短管的骑步枪,腰间挂着马刀,骑着高大的顿河马,眼神冷峻。他们曾是纵横淮上的淮右精锐,如今则是为李鸿章开辟安西大唐的利剑。
姚百万的商队走在最前头,他的骡马驮着粮食、布匹、铁器,甚至还有几门拆解的小炮。他骑着一匹高大的汗血宝马,时不时回头望一眼长安城的方向,嘴里嘟囔着:“走了,走了,再不回来了”
队伍中不时传来婴儿的啼哭声、老人的咳嗽声,以及车轮碾过碎石发出的刺耳声响。还有一些背着书卷,拄着长剑,结队西行的书生,都是大周太学的太学生,一边走还在一边背诵《论语》,仿佛不是在逃难,而是要将儒家名教的火种传播到西方的汉唐故土之上。
“让开!让开!”一队骑兵疾驰而过,扬起漫天尘土。他们是马新贻麾下的回部马队,这次负责充当西迁大军先锋,领头的军官一边策马飞驰,一边喊道:“渭河渡口已备好浮桥,各部按序过河!”
李鸿章策马来到队伍中央的一辆四轮马车旁,轻轻敲了敲车窗。
“皇上,”他低声道,“您找我?”
车窗的帘子被一只枯瘦的手掀开,露出曾国藩那张苍白如纸的脸。他的胡须已经花白,眼窝深陷,唯有一对三角眼依旧锐利。
“少荃.”他咳嗽了两声,“队伍走得如何?”
“还算有序。”李鸿章答道,“臣的骑兵稳住了阵脚,暂时没有溃散的迹象。只是.”
“只是什么?”
“粮草消耗比预计的快。姚百万说,照这个速度,到兰州前就得杀骡马充饥了。”
曾国藩闭上眼睛,长长地叹了口气:“告诉姚百万,从今日起,所有士绅的口粮减半。至于那些奴仆.”他顿了顿,“愿意跟着走的,每日发一升杂粮;不愿的,就地遣散吧。”
李鸿章眉头一皱:“皇上,这.”
“少荃,不要担心咱们在西边没有足够的国人!”曾国藩的声音很轻,语气冰冷,“人多有什么用?大清有四万万人,不还是亡了?我大周有三四千万人,不还是要亡了?少荃,若想在西边开辟一片疆土,关键不是人多,而是人狠!”
李鸿章一震:“人狠?”
夜幕降临,队伍在渭河北岸扎营。曾国藩的马车被特意安置在一处高地上,周围由最精锐的洋枪骑士把守。
李鸿章端着药碗走进马车时,发现曾国藩正就着微弱的油灯批阅文书。他的手指已经瘦得皮包骨,握笔时不住地颤抖,却仍坚持在每一份文书上盖上印信。
“皇上,该喝药了。”
曾国藩放下笔,接过药碗一饮而尽,眉头都没皱一下。
“少荃,坐。”他指了指对面的座位,“我有话对你说。”
李鸿章看了眼自己这个时日无多的老师,叹了口气,恭敬地坐下了。
“朕时日无多了。”曾国藩开门见山地说。
“皇上何出此言?兰州水土养人,您到了那儿.”
曾国藩摆了摆手,打断了他:“我自己的身子,我自己清楚。”他望向窗外,看着营地里星星点点的篝火,“纪泽.守不住这摊子。”
李鸿章没有接话。
“朕死后,会留下遗诏。”曾国藩的声音很轻,却字字清晰,“传位给你。”
李鸿章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惊愕:“皇上!这.”
曾国藩苦笑一声:“少荃,你就别推了!”他摇了摇头,“如今的大周已经名存实亡了。不大周从来都没真正存过,它不过就是名教的火种罢了。咱们师徒做的,就是为名教保下这一团火种!少荃,说说吧,你打算怎么挑起这重担?”
夜风穿过马车的缝隙,吹得油灯忽明忽暗。李鸿章沉默良久,终于开口:
“皇上,等到了河中,我打算效法西周。”
“哦?”曾国藩微微抬眼。
“定王畿于费尔干纳群山环绕之福地,封五藩于大河之畔、绿洲之中。”李鸿章的声音低沉而坚定,“畿内行名教之礼,以存儒家元气;五藩则因地制宜,以安河中万民。”
曾国藩闭上眼睛,似乎在思索。半晌,他缓缓道:“好好一个‘畿内名教,五藩安民’。”
他睁开眼,目光如炬,其言也善:“但你要记住——不要再想什么恢复中土,也不要折腾什么工业产业。河中还不如关中,我们没有那么多本钱去跟太平军拼枪炮。”
李鸿章深深一揖:“学生明白。”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曾国藩喃喃道,仿佛在对自己说,又仿佛在告诫李鸿章。
第二天黎明,号角声响起,队伍继续向西行进。
李鸿章领着数十个“洋枪骑士”,护卫在大周皇帝曾国藩所乘坐的四轮马车之侧,而在那辆四轮马车里,这位病入膏肓的大周天子靠在软垫上,望着窗外渐亮的天色,只是轻声念道:“少荃,名教的道就靠你了!”
美利坚,华盛顿。1861年6月6日。
白宫前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已经挤满了人。戴维斯总统和他的高级顾问咸丰并肩站在大理石台阶上,望着最后一队南军士兵踏着鼓点从白宫外走过。
罗伯特·李骑着他那匹名叫“旅行者”的灰色战马,走在队伍最前方。他身后是五千名俄国雇佣兵,清一色的灰衣和米涅式步枪,靴子踩在石板路上发出整齐的咔嗒声。这些打过第九次俄土战争的老兵的脸上没有表情,仿佛只是去参加一场围猎。
“太慢了……”咸丰突然开口,声音压得很低,只有戴维斯能听见,“拖拖拉拉几个月,才凑出五万五千人,八十多门炮……这点兵力,怎么打垮北方?”
戴维斯的手指在西装口袋里捏着一枚金币——那是佐治亚州议会送给他的纪念币,上面刻着“州权至上”的字样。
“美国总统不是独裁者。”他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美利坚合众国的军队由各州民兵组成,联邦无权越过州政府强行征召。国会没有批准战争拨款前,我连一门炮都不能多买。”
咸丰侧过头,看着这位南方总统的侧脸。晨光映在戴维斯的金丝眼镜上,镜片后的眼睛中散发出的是一种不应该出现在的清澈咸丰心想:我和老六当年一定也和现在的你一样蠢,根本不知道大清是个什么东西!
“总统,您守护的到底是宪法……”咸丰轻声道,“还是棉花和种植园?”
戴维斯的表情终于出现了一丝裂痕。他猛地转头,镜片后的瞳孔微微收缩:“赵先生,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远处,南军的炮兵车队正缓缓驶过。十二磅拿破仑炮的炮管看着倒是威风凛凛,只是已经过时.
“北方有工厂、铁路、钢铁……”咸丰望着那些大炮,声音平静得像在讨论天气,“而南方只有棉花。总统先生,您真的相信,靠这些”他指了指正在行军的队伍,“真能打赢一场工业化战争?”
戴维斯沉默了片刻,突然笑了。
“赵先生,您不了解美利坚。”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枚金币,在指尖翻转,“北方确实有工厂,但欧洲的列强都支持我们!”
他们也曾经支持大清.咸丰同情地看着戴维斯。
“英国兰开夏的纺织厂,每天要消耗我们南方五十万磅棉花。”戴维斯的声音中却带着近乎虔诚的笃定,“伦敦的银行家们可以假装关心黑奴,但他们绝不会让自己的机器停转。”
咸丰望着远去的军队,突然叹了口气。
“总统先生,您有没有想过……”他低声道,“如果有一天,英国人找到了新的棉花来源?比如印度?或者埃及?”
戴维斯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沉默。一名传令兵飞驰而来,在台阶前勒住缰绳,战马前蹄高高扬起。
“急报!北军的主力正在哈里斯堡集结!兵力至少七万!”
戴维斯的手指猛地攥紧了那枚金币。咸丰瞥了一眼他发白的指节,轻轻摇了摇头,然后语气肯定地说:“会赢的这次会赢的!但南方需要尽快集结更多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