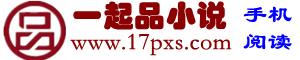第三十五章 对自我的疑惑
作品:《晋庭汉裔》 最新网址:www.xs.fo</p>司马遹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但对于洛阳的政斗而言,一切才刚刚开始。
太子离开洛阳之后,皇后听闻有许多人参与送别太子,当然是勃然大怒。她自认为斗倒了太子,再度权倾朝野,又恢复了以往跋扈的作风。立刻派人向司隶校尉满奋下令,誓要将那些目无君上之人统统抓进牢狱。大有一副要以此为契机,对太子党进行大肆清洗的架式。
可结果出乎皇后意料,这次本应该伸张她无上权威的行动,很快就变得乌烟瘴气,沦为一地狼藉。
首先,要抓捕的人实在太多了。这次送别太子,不知有没有人暗中鼓动,算上平民竟有上万人之多,虽然洛阳是个有数十万人口的大城市,人力不值一提。可如此庞大的人数,显然也超过了可以抓捕的范围,就连列举犯人名单都极为困难。
其次,即使不算平民,仅抓捕违令的官宦子弟,这倒是好办。可即使如此,要参与的人员也依旧有上千人。满奋带着衙役四处抓人,对方也并不拘捕。
可讽刺的是,洛阳的监狱却有些不够用了。
在洛阳的监狱一共有四个,司隶校尉主管的司隶狱、廷尉主管的诏狱、河南尹主管的河南狱,洛阳令主管的洛阳狱。其监狱之大,种类之繁多,是全天下所有城市都无法匹敌的。
即使如此,洛阳的监狱也很快人满为患。数不胜数的世家子弟被塞到监狱里,往往七八人共用一个牢房,人挤得像是满仓时的麦米。其场面之壮观,恐怕还要超过了当年汉灵帝的党锢之祸。
而最重要的是,场面纷乱到了这个地步,负责监狱的主官也不愿听从皇后的命令,承担迫害太子党的责任。
河南尹乐广率先表态,他作为名声不下于王衍的士族领袖,将河南狱内的所有囚犯全部释放,并且公然表态。如果皇后与鲁公要追求此事,他甘愿受罚。
而司隶校尉满奋是个人精,他压根就不把犯人往司隶狱里带,得知乐广在河南狱大肆放人。他干脆把犯人全送到河南狱去,出了事也由乐广担责,好名声却是一起共享。
洛阳令曹摅不敢像乐广这般做,但也经受不住压力,托关系找都官从事孙琰去劝说贾谧:“您之前废黜太子,宣扬的是太子作恶多端,罪无可赦。可现在愿意为太子入狱的人却如此之多,真关进去了,不是宣扬太子得人心吗?还是把大家都放了吧。”
贾谧也没想到事情会闹到现在这个地步,现在清洗已经发展成闹剧了,再坚持也毫无意义,最后只得同意。他连忙进宫面见皇后,废除了抓捕的诏令。
不过短短三四日,后党原本声势浩大的清洗行动,竟然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皇后也从中察觉到了统治的危机,于是便按照此前计划,放出了想要立淮南王司马允为皇太弟的风声,试图以此抵消罢免司马遹的恶劣后果。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不过是缓兵之计。想要立皇太弟,直接下旨即可,何必弯弯绕绕地进行试探呢?
事实也正是如此,宫内有人传出消息,说皇后已经足足两三月不见人了,她自称是有了身孕。若是等这个孩子生下来,是个男儿,必然就是新太子,哪里还轮得到淮南王呢?
可算算年龄,大家又觉得不对,皇后今年已经四十三岁了,上一次怀孕还是在十三年前,按理来说,这个年龄要怀孕是很困难的。何况为什么早不孕晚不孕,偏偏是这个时候怀孕?
因此,很快就有人猜测说,听说最近韩寿与贾三妹新得一子,皇后莫不是要进行那偷天换日,把皇位变成他们贾家的吧?
这个猜测无凭无据,但几乎一夜之间风靡全城,都说得煞有其事。原本还没有张狂几日的后党,此时看舆论如此倒向,顿时又偃旗息鼓起来,就连鲁公贾谧,此时都躲在金谷园内不愿见人,似乎只要等上一段时间,一切纷争都会烟消云散。但一切果真如此吗?
就连王粹都感觉到态势不对了,他对刘羡说:“奇怪?我还以为皇后和鲁公已经掌控局面了,怎么几天下来,搞成了现在这幅德性?他们是怎么斗赢太子的?”
刘羡对此早有预料,他解释道:“弘远,太子不是皇后斗赢的,他是输给了人心。”
“人心?”王粹大惑不解。
“是的,是人心,我也低估了人心。如果说人心是一条河流,在武皇帝死后的这十年,大概就是人心的严冬。”
这段时间,刘羡一直在反思自己回到洛阳的所作所为,到底是哪里出现了巨大的失误,此前他身在局中,有些事他看不出来。但当失败的结果已经摆在面前时,他终于多多少少理解了一些现状:
“妖后与贾谧,试图将权力永远把握在自己手里,用阴谋来构陷对手,用武力来威慑天下,他们只知道索取,却不知道付出,看似还大权在握,将世上本就不多的信与义毁坏得一干二净。人心已经冷了,十年来,这条河流的表面已经结成了一层坚不可摧的坚冰。”
“大概妖后还为此沾沾自喜吧,她凌虐了人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竟然令天下江河都不敢东去。”
“可在这片土地上,何时有过永远封冻的河流?坚冰之下,是数之不尽的暗流,大家只是在伪装,积蓄力量,同时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将河冰化为一场不可阻挡的凌汛。”
“而太子就是这个阻挡凌汛的河堤。”
刘羡闭上眼,长叹了一口气,徐徐道:“可皇后不仅不明白这一点,还认为这道河堤约束了自己的权力。于是主动掘去了这道河堤。”
“太子这道河堤,不动时岿然如山,看似无可撼动。但他承受着江河最大的压力,下面早已是千疮百孔了。只需要有人轻轻一推,那就会轻松垮塌。皇后怎么会不能成功呢?我也是现在才明白,太子的局面,从晋武帝传位给当今天子开始,就已经是一个死局了。”
王粹闻言,也不禁想起了早年齐王党争的往事,颔首道:“或许先帝传位给齐王,就不至于此了吧。”
刘羡没有接话,他躺在床榻上,精神还沉浸在刚才的反思之中,想着一些不适合说出来的事情。
其实这些是老师陈寿早就教导过自己的事情。他第一次教导自己信与义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世界失去了信与义,人们就将化为禽兽,不断地相互厮杀下去,将人世化为一片废土。现在发生的一切不就是这个道理的应验吗?
而自己原本的想法,竟然是想依托于司马遹这座晋室最后的河堤,来换取复国的机会,这何异于痴人说梦?其实从来没有人支持过司马遹,哪怕是自己也是如此。想要这样来取得政变的成功,完全就是抱薪救火,从一开始就是自相矛盾的。
刘羡仔细想来,其实自己并非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但自己有些太过矛盾了,他既想要复国,同时也不愿意向贾谧做起码的屈服,更不愿意背信弃义,去转投另外的阵营。以致于司马遹其实并没有拿出一个令他信服的政变方案,可他还是将信将疑地执行了下去。
为什么会如此呢?自己怎么做才是对的呢?在这个混沌黑暗的政局之中,刘羡全然看不见一条能让自己满意的道路。事实上,从三月回到洛阳的时候,他就一直怀有这样的困惑,直到今日还没有解决。
而在司马遹被废黜的当天,他的内心反而生出了更巨大的疑惑:为什么自己看好的人,最后总会陷入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呢?
刘羡随即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问题。司马遹等人遇到的问题,也是他个人的困境。在一条大河将要摧垮河堤,在荒野肆意横流的紧要关头,似乎个人的选择是如此的渺小。人与人之间的对错,根本无人在乎。
老师陈寿在临终前曾经告诫过,这或许将是一场持续数百年的大乱。与其试图力挽狂澜,不如想办法激流勇退,离开权力的中心,精心经营自己的家族。总而言之,在动乱之中,存在才是一切。
但在刘羡看来,遇到挑战便逃跑,这是懦夫的生存哲学,他实在不能容忍自己成为一名懦夫。可要想为未来想出一条出路来,他又实在难以想象。
刘羡一时陷入了死胡同内,他在病榻上辗转深思。无论在白日中,还是睡梦中,都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可越是思索,他越是觉得自己无路可走。
莫非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荒谬,相信信义的人,竟然会沦落到走投无路吗?
到了这个时刻,刘羡忽然能够领会到老阮公和孟子的心情了。一个能写出“视彼庄周子,荣枯何足赖”诗句的人,为何会狼狈到穷途之哭呢?一个能说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人,为何会说出“穷则独善其身”呢?
想到这里,刘羡有些心灰意冷。说实话,如今的遭遇,并非是刘羡一生中最大的挫折,至少远远不及九年前。可它引起了刘羡对自我的疑惑。虽然疑惑是人生的常态,但对于心智已经成熟,并且胸有大志的人而言,迷惑与彷徨是更不可接受的。
他自言自语说:“不论如何,只有闯出一个名堂,才能对得起那么多死去的人。”
“许多困难我都想到了,也解决了。这一次也不例外,我相信,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山,也没有走不通的路。”
大概又过了七八日,右肩的伤口初步愈合,已经能够简单活动的时候。刘羡便想要强迫自己忘却这种迷茫。放在以往,他会舞剑,舞得大汗淋漓,让自己无暇多想,只靠本能来战斗。现在既然有伤不能舞剑,刘羡便找王粹要了一根竹笛,他打算用音乐抚慰内心的忐忑。
愤懑的刘羡此时渴望战斗,因此,他吹的乐曲也是激扬的《甲士列阵曲》,似层层铁骑踏地而来,飞鸟惊起,猛兽骇奔。又似雄浑沧桑之天地,向孤独的人压迫而来。刘羡将自己的情感融入曲内,吹到后面,曲调与节奏越发高昂,凄切与悲壮同奏一处,哀怒交织之间,更似有闻鸡起舞,听鼓踏阵之感。
一曲吹罢,并不能消尽他心中愤慨,于是他便反反复复地吹奏。就好像自己重新回到了关西的战场上,正身骑在翻羽上,头上是漫卷的旗帜,脚下是飞驰的平地,身上是滚烫的热血,耳边是箭矢的鸣叫,眼前是冰冷的刀锋,天地苍茫,只有杀敌是唯一的任务。
由于吹奏的地点是在后院,襄阳侯府的下人们可以听到音乐。王粹此时又不在府内,他们便好奇地围聚过来。等刘羡结束的时候,不知不觉已经有了许多旁听的人。
他们为刘羡的曲声喝彩,并赞美说:“使君吹的真是壮士曲,哪怕我们从来没有上过战场,听了也勇气倍增呢!”
看见这些笑脸,刘羡的心情也舒缓了很多,便和他们开玩笑说:“你们想听什么,我也可以吹给你们听。”
不料话音一落,下人们顿做鸟兽散,弄得刘羡不知所以。一回头才发现,不知何时,颍川公主司马脩华竟然站在了自己身后。他连忙要起身行礼,口中说道:“见过殿下。”
脩华看着刘羡手中的笛子,似乎想起了许多事情,很快摆手说:“你有伤在身,何必行礼呢?”
又说道:“还记得当年吗?你在五兄府上的时候,也给我吹过曲子,没想到,一转眼就过了这么多年了。”
刘羡觉得有些尴尬,按理说,公主是王粹的夫人,也就是女眷,此时两人应该避嫌才对。作为一个经典的封建卫道士,此情此景,刘羡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好在有人打破了这种尴尬。
这时候,有一个侍女快步趋走过来,一脸不知所措地对公主道:“殿下,赵王长史孙秀来访。”
“他说,想要见刘使君一面。”
刘羡放下竹笛,心想:该来的终于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