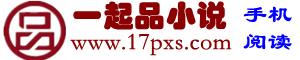第八百六十六章 艺术的生活
作品:《全能大画家》 最新网址:www.xs.fo</p>“只有完全的理解,才能学会去爱。”——酒井太太。
——
顾为经最初朦胧想象里,改变会是完全相反的……就算这不是什么印第安纳·琼斯式样的神秘大冒险,也会是一场充满艰辛的旅程。
它会是朝拜式样的故事。
苦行。
磨砾。
先是烈火真金,然后金钢不坏,最后大彻大悟。
卡拉会在旅途里变得越来越坚硬,越来越强健,变成了拥有刀锋一般颌线和美黑皮肤的女性健体运动员式的形象,如挺举120磅的杠铃一般,一声大喝,将沉甸甸的命运高高的举起。
这种想象不能算全然的错误。
人无法通过信件文字,乃至画作,就在脑海里想象出对方的外表的对吧?
酒井大叔的作品如女子一般细腻柔美,笔触给以人光滑无瑕的感觉。据说,一次匿名交流展会上,曾有一位关东书法家无意间瞧得酒井一成的一张作品,惊为天人,和友人大赞说此画极为灵秀,缠绵悱恻。
更妙的是,它有一种极为“纤细”的美感。
书法家叫人拿来纸笔,当场引了汉词的“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九个字,说创作者轻盈的好像能在这荷叶上跳舞,他斗胆一猜,画这幅画的人大概是位秀美的女性艺术家。
后来展会上。
他看到了体重接近250磅的酒井大叔乐乐呵呵间一弹一弹的滚上主席台,久久的沉默不语。
世上大约找不到能托举着酒井一成,让大叔在上面蹦蹦跳跳,欢快起舞如风的荷叶。
卡拉却未必不能举起120磅的杠铃,流畅而富有力量感的肌肉美,当然也很漂亮,也很高贵,就像来自奥林匹亚的女神。
但是,在这一封封的信里,抽象意义上的卡拉,精神意义上的卡拉。
她正在变得越发的细嫩而敏感。
她会大段大段的给弟弟讲述人们是怎么用面粉菜叶以及适量的动物脂肪,去烙一种锅盔式样的饼子的,她会讲述茅草屋外,猎人怎么晾晒着动物皮毛。她见到当地的女人们怎么纺织棉花。
她讲述起了一行人跟随向导从一个城市旅行到了另外一座城市,马车队在布满黄沙的路上穿行,黑压压的鸟群穿过远方的山谷回巢,风很大,她们以及四周的马车上的布料,行人兜帽头纱如何纷纷鼓起了风,如万丈黄尘间穿行着的沙海行舟。
“纳尤基”——卡拉旅途之中的一位所聘请的本地向导的名字,据说是一位山区上了年迈的猎人,在信中几个让顾为经印象最深刻的人之一。
他在卡拉的信中多次出现。
两个人的语言完全不通,仅仅只能通过翻译来做简单的交流,纳尤基非常习惯于沉默,很多时候,人们几乎都忘记了他的存在。但他又极为有趣。
顾为经留下深刻印象在于,卡拉在文中反反复复的多次使用了“高贵”这样的形容。
纵然安娜在读信的时候,把德语直接翻译为了英语。
顾为经相信,这里面应该不存在信息二手加工的理解错误。
他所听到的,安娜所读出的,以及卡拉所写下的,应该都是“高贵”这个单词。真奇怪,那是卡拉·伊莲娜,她的亲生父亲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帝国的高等伯爵,她的前半生有大半的时间,在各种各样的宴会、沙龙里度过。
她对自己的父亲大加嬉弄,却在信中称一位年迈沉默的本地土生土长的老猎人,是她一生中所见过的最有高贵感的人之一(“纵然,每次想要和他多谈些什么的时候,都彼此沉默对望,然后铩羽而归”卡拉这样写到)。
这个说法是为了激怒她的父亲么?
大概不是吧。
卡拉有一封长信,前面整整三分之一,都在讲述纳尤基乌黑色的眼睛,说那双眼睛时而流露出善意,少数的时候,会流露出愤怒,更多的是沉默。
宁静而睿智的沉默。
从未有过一次,有任何轻挑或者诙谐感从那双眼睛里涌现过。
卡拉说,尽管有些时候,她觉得纳尤基从未真正发自内心的欢欣快乐过,就像她从未觉得纳尤基真正发自内心的恐惧不安过。
但这是她一生中见过的最为“高贵庄重”的眼神。
是的。
又一次的。
卡拉使用了高贵这个词汇,以及庄重。
“我完全无法想象,有这样眼神的一个人有一天会诙谐的哈哈大笑,喝个烂醉,或者恐惧的瑟瑟发抖是什么模样,就像我无法想象,他像我生活中的很多男人一样——”安娜读道,“穿着紧身短裤,进行赛艇比赛或者手拿一支板球拍,到底是什么模样……”
那封信的后三分之二。
卡拉则记述了纳尤基,怎么在一天休息的时候,用陷阱捉住了一只猞猁,它的血水流淌到了卡拉的手上。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若借用卡拉自己的语言来形容,这些信为顾为经够勒出了一个形象,那就是——这里既不是理查德·伯顿里的故事,也不是《一千零一页》神话传说里的故事。
卡拉离开巴黎的时候。
她是抱着见到些“什么”的心态出发的。
后来。
她发现,这里既不是冒险里的世界,亦不是童话故事里的世界。
这里就只是世界。
没有睿智高贵代表着理性与文明的绅士冒险家,也没有阿里巴巴四十大盗,以及深山里满仓的黄金宝藏。
童话里的世界丰富多彩,云遮雾绕,神秘绝伦。
真实的世界。
只要你足够敏锐细腻,那么风沙会吹到你的脸上,血的温度会在你的指尖流淌。
——
“……再一次的回到巴黎——”
安娜读着她手里所拿着的最后的一封信,卡拉完成旅行后,在巴黎寄给家庭的长信的结尾。
“我决定要当个专职的画家。就这样吧,这是我的最后决定。”
“另:我把一幅画藏在了远方,你永远也找不到。”
“——卡洛尔。”
这封信通篇写的很简练朴实,结尾处的署名同样也是。
早期的那些信里,卡拉必然有的环节,便是在写给父亲的信里,在结尾处做出尖刻的挖苦。
慢慢的。
那些文字消失了,卡拉的结尾越来越简单,一句礼貌用语,一个名字,或者只有一个名字,一个字母K。
到了这封信。
则变为了“Crol”。
安娜弯下腰,把这封信很小心很小心的放在了茶几上,动作轻柔细嫩的如同弯下腰,把卡拉的魂灵揽入怀中。
直到抵达命运的终点站,当永恒的寂灭或者天国与来生到来的时候。
力量。
卡拉在旅途中得到的惊人力量,她都始终陪伴着她。
人往往是要经历些什么,目睹些什么,才能获得真正的改变。
可也许踏上旅途的不只卡拉一个人,那些冒险家们和卡拉一样,都曾目睹过相似的场景,为什么卡拉得到了和他们截然不同的视角呢?
这不是“伊莲娜这个姓氏”的魔力。
这是共情的魔力。
列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库尔贝、杜米埃……这个咒语的伟力在艺术史上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显现,且从来没有褪色过。
安娜知道,卡拉也不一定能真正的称之为共情。
那是一场极长的旅程,可放在整个时代背景之下,亦只是浮光掠影一般的短暂一瞥。
做为一个女人,在那个时代,她几乎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中,便真正的在旅程中完完全全的融入四周的风土人情之中。
无论她带着什么样的目的出发,这都是客观事实。
带着20000英镑的支票和仆人万事通先生踏上环球旅程的福格先生做不到。
卡拉·冯·伊莲娜小姐同样也做不到。
她带着充足的现金,法朗、英磅,奥斯曼里拉,带着使女和仆人,有支票和手枪,需要的情况之下还会聘请很多护卫。
这些东西一起构成了卡拉身外的那层泡泡,把她和真正的苦难隔绝开来。
卡拉并非是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画家。
她是一个印象派的画家。
比起那些真正的融入底层人们真实生活的巡回展览画派画家的画家们,卡拉其实也是有所不同的。
她进行的仍然是一场微缩风景水晶球似的旅行,无论她是水晶球里面的那个,还是水晶球外面的那个。
都一样。
就像从始至终,卡拉很努力的尝试了,却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和那位她留下深刻印象的老猎人纳尤夫亲自沟通上一句话。
这大概也是卡拉的遗憾。
但她依然从这场旅行中收获了什么。
如果收获的不是共情,那就是力量,如果这不是批判现实主义式的对世界的深刻理解,那么就是印象派式的对自我的深刻理解。
如果这不是列宾。
那么则近似于梵·高。
安娜总是想,改变是如何的发生的,从小在贵族家庭上流社会里长大的南丁格尔,她本可能以安逸富贵的度过一生。她从小照顾过生病的祖母。
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那种人间炼狱一样的场景彻彻底底的惊呆了南丁格尔,她看着人们在战场上哀号的死去。
她告诉自己,人们是不应该这样去死的。
而也许。
那场历时一年的旅程,对卡拉·伊莲娜来说,便是这样生命里至关重要的思考时刻——
人们应该怎么样活着。
她开始想要看宏伟的视觉奇观。
后来。
她渐渐的感受到了,真正宏伟的东西,从来不是在君士坦丁堡城墙外的大海上喷吐着雄雄希腊火的烈焰战船,也不是躲在布帘帷幕之后,偷听臣子们谈话的年幼苏丹。
真正宏伟的奇观,也许从来都隐藏在吵闹的她无法入梦,喧嚣的令人绝望,让她想要“像猫一样跳脚”的巴扎之中。
隐藏在人间的喧嚣之中。
也许,整个旅途中,她都没有思考过复杂的政治博弈,深刻的社会制度,帝国的海外利益,或者其他搅动着世界风云的东西。
她只是凝视着猎人的眼睛。
感受着他那种顽强的生命力。
人是可以宁静的对抗命运的,人是可以背负着命运前行的,人也是可以像是捉住一只猞猁一样,捉住命运的。
无论命运意味着什么,贫穷还是其他什么,还是……伟大的伊莲娜家族。
这和能力无关。
这只和勇气与斗志有关。
卡拉做出了选择。
她不是在跳上船,跳上列车,离开巴黎或者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时候做出了抉择。
她是在理解这一切之后,才真正的做出了抉择。
安娜很小时候听过长辈说一些口口相传的故事,据说,把女儿抓回来关到地窖里后,老伯爵也很崩溃。
有很多仆人都听到过。
一向讲究体面和威严的伯爵先生抓着乱蓬蓬的头发,几乎是在歇斯底里的怒吼,亦几乎是在歇斯底里的乞求——
“不知道你在法国中了什么邪!”
他说巴黎果然是让人道德败坏的城市。
他还说……说,求求你了,求求你了,我认真的求求你了好不好,我求求你不要再闹了。
甚至有人见到老伯爵先生,日常穿着骑兵团上校军装的男人,疑似在书房里默默的流泪。
安娜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她只觉得老伯爵很虚伪,觉得虚伪简直就像是伊莲娜家族基因里的劣根性,他把女儿关进地窖里活活的折磨到死,又在那里可怜巴巴的哀求,说求求你了。就像他一边宣称自己热爱艺术,又把女儿关进地窖一样的虚伪。
长大后,安娜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老伯爵,她的先祖,当时的哀求未必真的不是发自内心,他所流下的眼泪,也未必就真的只是些鳄鱼的眼泪。
也许情感都是真的。
只是老伯爵先生始终理解错了一件事情,他始终都把卡拉当成一个闹脾气不听话的人去看。
不。
卡拉不是在闹脾气。
刚刚踏上旅程的时候,在信件里写下那些抱怨的时候,或许是。
但后来可能就不是了。
在她返回巴黎的时候,在她以卡洛尔之名,寄信给家中的时候,在她说“我已经下定决心,决定当个画家”的时候。
一定不是。
真遗憾。
卡拉写了一封又一封信给家里,但老伯爵始终没看懂。
安娜读了一封又一封信,她把最后一封信放在茶几上,抬起头,想要看看顾为经有没有听懂。